
在日前正在法国举办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上,中国著名摄影理论家藏策作为受邀专家,在摄影节上做了《从巴特到“元影像”》的演讲,得到了国际学者们的高度评价。法国学院书籍与知识部副主任朱笛特·郈兹称藏策是一个给他们带来了震惊的学者。学术活动负责人娜塔莉·拉括认为藏策对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让法国的符号学有了中国的维度。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研究专家马修·麦塞哲说:在这个“巴特又回来了”的主题中,我们看到巴特也从中国回来了——法国符号学经过中国理论家的改造,今天又“回家”了。
巴特对于摄影的分析,其实更多是从普通的私人家庭照片,以及新闻照片、广告等切入的。藏策在讲演中对此认为,巴特对于摄影领域的这种偏重个人感受式的介入,却更加促进了摄影向着另外一条路径的转向。以往的摄影,主要是摄影师沿着对影像自身的探索而进行的,所谓的摄影理论,也主要是对于摄影经验的归纳。比如安塞尔·亚当斯的“区域曝光理论”、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等等。而巴特对于摄影的探索方式则与他们不同,巴特是站在影像之上的层面上来分析影像的。而这种来自巴特的符号学方式,给正日益受到观念艺术等思潮影响的摄影师们带来了新的启示。摄影发展的路径由对影像本身的探索,过渡到了由学术及理论所引领的摄影实验。这也正是巴特之于摄影的重要意义所在。

对于为何把巴特的艺术思想作为自己摄影理论研究的重心,藏策表示,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巴特是随着各种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而被介绍到中国的,此后逐渐在中国的知识界声誉日隆。然而直至今日,中国学者对巴特的研究仍主要在译介和阐释的层面上进行,却很少有人能在巴特之后继续推进他的各种思考。这种状况让他想到了古代中国对于佛学的发扬光大与“倒流”回印度的盛况。今昔对比实在令人汗颜!于是他选择了在汉语的世界中继续推进巴特式的思考。他表示,自己的理论灵感已不仅仅来自巴特,同时也参考了格雷马斯、雅克·拉康以及福柯等人的理论。他于2001年发表了以《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为总标题的六篇论文,第一次将符号学的方法应用于中国的摄影理论研究。其后他又提出了“元影像理论”(théorie de la méta-image),并与中国的摄影师们一起进行了多次颇具影响的影像实验。
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是世界上创办最早、最具影响力的摄影节之一。藏策是首位受邀在这个摄影节上做学术演讲的中国理论家。近年来,中国摄影发展迅速,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摄影家参与国际交流也日益频繁,但中国的摄影理论研究却一直未能走向国际。藏策受邀在阿尔勒摄影节的演讲,是中国理论家第一次走上国际讲坛,是中国摄影理论步入国际学术界的一个良好开端。来自韩国的著名策展人宋修庭女士也来到了阿尔勒,向藏策表示祝贺。
藏策是我国的著名文学与艺术理论家,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奖),以及济南国际摄影节“最高学院奖”等多项大奖。他的艺术符号学研究方法源自法国学术,但又经过了他的学术创新,加入了源自东方智慧的维度。他创建的“超隐喻理论”和“元影像理论”,在国内有着很大的影响。连续两届的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就都是以“元影像理论”作为学术框架的。“元影像理论”还引领了一系列的影像实验活动,如《隐没地》影像实验,就曾为包括央视在内的国内300余家媒体报道,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由藏策作学术主持的“乾坤湾影像实验”“华山新风景影像实验”等也都是近年来中国摄影界中的亮点。藏策个人的观念摄影作品《格林威治时间》,也在广州、西安、宁波等地参加了巡展。#p#副标题#e#
从巴特到“元影像”
女士们先生们:
诸位好!
我是来自中国的藏策,我在我的国家,在汉语的世界里,一直继续着罗兰·巴特式的符号学研究工作,继续着他对影像奥秘的探索。非常高兴在阿尔勒与诸位相聚!
我们这个工作坊的题旨“巴特回来了”,让我联想到了巴特在《明室》中,对于他母亲生前照片的精彩分析,对于当时的巴特来说,在凝视母亲照片的那一刻,他的母亲也“回来了”。巴特因而也确信:“摄影真谛的名字是‘这个存在过’ (ça a été)”。而刚刚马修先生则对我说,你的研究表明,巴特也可以从中国回来。
巴特对于摄影的分析,其实更多是从普通的私人家庭照片,以及新闻照片、广告等切入的。他在《明室》的《私生活/公众生活》章节里甚至说:“业余爱好者通常被说成不成熟的艺术家:一个不能——或不愿——上升到专业水平的人。但是,在摄影活动领域里却相反,达到专业顶峰的往往是业余爱好者:离摄影真谛最近的,正是这种没有上升到专业水平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也要向大家展示几张由完全没有经过摄影训练的中国农民拍摄的照片,希望大家能从中发现“刺点”。这些照片源自我们在中国进行的一个影像实验,由数十位艺术家与当地农民共同参与,农民拍摄了大量精彩的照片,这几张只是其中极少的代表。
下面让我们继续来讨论巴特,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巴特对于摄影领域的这种偏重个人感受式的介入,却更加促进了摄影向着另外一条路径的转向。细细想来,这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是摄影界对于巴特的一种很奇妙却又富于创建性的误读(lecture fausse)。以往的摄影,主要是摄影师沿着对影像自身的探索而进行的,所谓的摄影理论,也主要是对于摄影经验的归纳。比如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的“区域曝光理论”、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HenriCartier -Bresson )的“决定性瞬间理论”等等。而巴特对于摄影的探索方式则与他们不同,巴特是站在影像之上的层面上来分析影像的,他所探讨的其实是有关影像的影像(我称之为“元影像”: méta-image)。而这种来自巴特的符号学方式,给正日益受到观念艺术等思潮影响的摄影师们带来了新的启示。摄影发展的路径由对影像本身的探索,过渡到了由学术及理论所引领的摄影实验。这也正是巴特之于摄影的重要意义所在。不过在我看来最为有趣的是,以学术与理论为核心的摄影路径,最终却又挑战了巴特所谓“这个存在过”(法文原文:ça aété)的摄影真谛。尤其是在被称为“后摄影”时代的今天,各种“不曾存在过”的虚拟影像正在颠覆并超越巴特当年对于摄影的认知。这大概是巴特当年所始料未及的吧。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理论研究者和艺术家,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巴特在中国的影响以及我本人所受到的启发。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巴特是随着各种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而被介绍到中国的,此后逐渐在中国的知识界声誉日隆。然而直至今日,中国学者对巴特的研究仍主要在译介和阐释的层面上进行,却很少有人能在巴特之后继续推进他的各种思考。在文学、艺术以及摄影的批评界,人们对于符号学以及各种话语分析理论仍然感到陌生。这种状况让我想到了古代中国对于佛学的发扬光大与“倒流”回印度(le retour àl’Inde)的盛况。今昔对比实在令人汗颜!于是我选择了在汉语的世界中继续推进巴特式的思考。当然我的理论灵感已不仅仅来自巴特,同时也参考了格雷马斯(A.J. Greimas)、雅克·拉康(JacquesLacan)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理论。
我于2001年发表了以《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为总标题的六篇论文,第一次将符号学的方法应用于中国的摄影理论研究。首先,我将摄影视为一种“提喻”(synecdoque)。这既是针对摄影对空间的抽象而言,也是对其时间性的维度而言的,就如巴特所说“时间被卡住了脖子”(法文原文:“leTemps est engorgé”)。在这些文章中,我受巴特有关“神话”(mythe)论述的启发,又参照了解构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超隐喻理论”(théorie del’ultra-métaphore)。这是一种专门分析汉语中权力话语编码的理论,涉及到文学与艺术的“元语言”分析(analyse métalinguisque)。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超隐喻与话语流变》(Ultra-métaphore et flexion du dixcours)一书。其后我又提出了“元影像理论”(théorie dela méta-image),并与中国的摄影师们一起进行了多次颇具影响的影像实验。
就如巴特在《明室》中所言:“影像的本质全然是外在的,没有内心的东西,但它比最深层次的思想更难接近,更加神秘;它没有意义,却又能唤起人的一切感觉所能有的最深切的东西……”而我个人则认为:摄影本身只是一种现代科技的媒介,在摄影的层面上是解决不了摄影问题的,需要在观念的层面上解决;而观念本身又解决不了观念的问题,需要在哲学的层面上来进行思考;可哲学也同样无法寻得所谓的“真理”,哲学不过是一种认知的方式而已,所以哲学的问题又需要在思想的层面上来解决;而真正的思想是源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在灵魂的层面上进行。这正是“元影像理论”(théorie dela méta-image)的一个基本思路。
我们知道,巴特在晚年对古老的东方智慧颇有会心,在他开设的《中性》(Le Neutre)课程中借助了中国的道家思想来阐述他的“中性”。在此我也想说一点我个人在消弭二元对立(opposition binaire)方面的心得。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对立,就是文明与反智(contre-intellectuel)的对立。然而反智其实又恰恰是文明的”影子”( ombre)——因主流文明的压抑而得不到分化与发展的结果。所以,纵观历史上的种种纷争,也只不过都是人类在与自己的影子作战。
谢谢诸位!#p#副标题#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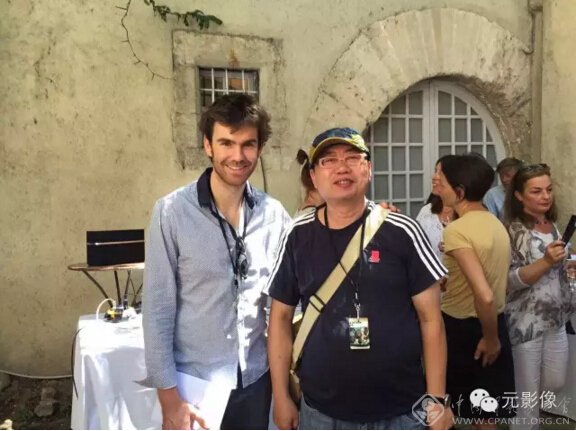
藏策对马修先生的回应:
马修先生引用了巴特的话:“一种影像,从本体论上说,就是什么也不能说:为了谈论影像,必须有一种非常艰难的特殊技艺,影像描绘技艺”。
我也引用巴特的两段话,来说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巴特说:“在照片的情况里,因为——至少是在文字讯息的层次上——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并不属于‘转换关系’,而是属于‘记录关系’,并且无编码显然在增强照片的‘自然性’的神话:场面在此,它是机械的但非从人的方面来被获取的(机械性在此是客观性的保证);人对于照片的介入(取景,距离,灯光,朦胧,运动线条)都属于内涵平面;一切就好像在最初(即便是空想的最初)就有一幅毛坯照片(正面的、清晰的照片)那样……”(这段文字见于巴特《显义与晦义》原文【L'obvie et l'obtus】,p. 35)。
此外巴特在《明室》下篇36节里比较了语言文字(说)与摄影的不同:“这种肯定性,任何文字的东西都不能给我。自己不能证实自己,是语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的乐趣所在)。语言的本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肯定的方式说:语言从本质上说是虚幻的;为了使语言变得不虚幻,必须采取一大套手段:要求助于逻辑,或者,如果不合逻辑,就求助于誓言。但摄影对任何中介物都不感兴趣:它不创造什么;她就是证明的化身。”
至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如果将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广义语言观,引入到我们的讨论中,问题就会变得明晰起来。阿多诺认为:“整个自然也充满了无名的未曾言说的语言。”人的语言是对事物的语言的翻译,把事物的语言翻译为人的语言不仅仅是将无声的翻译为有声的;而且也是将无名称的翻译为有名称的。那么摄影则是将事物的语言的痕迹留在了照片上,其不可被人类语言所转译的恰恰是真正属于摄影的,而这也正是其不可说的部分。
2015年7月8日下午
于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巴特又回来了”学术主题工作坊



 首页
首页 来源:《中国艺术报》
来源:《中国艺术报》 责编:黎语
责编:黎语 2015-07-24
2015-07-24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84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847号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 各团体会员微信公众号集成平台
各团体会员微信公众号集成平台